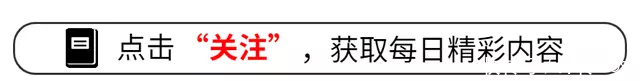作者:江寻
编辑:渡水崖
“今晚乒乓球混双决赛咯。”七月三十日上午,我往家庭群里扔了一条信息,随后又补上一句:“对阵朝鲜队哟。”企图将看点拉满。
“今晚回去看看。”老妈回复了我,连带一个呲牙笑的表情。而我亲爱的老爸,没有答话。
“老爸当了一辈子教练,不想再看体育比赛了。”这是有一次,我已经上大学了吧,暑假在家,打开体育频道看篮球赛,随口问了一句,得到这个回答。
“哦,好吧。”那时我二十出头,还太年轻,掂量不出这句话的分量。
二年级的时候,我识字不少,眼尖,在教科书上发现了老爸的名字。
那是《思想品德》的副册,我们当地编写的大事记。我指着那一页照片中的老爸对同学说,看,这是我爸,还有他的学生。同学朝我翻了个白眼,你骗人。
老爸确如他所说的,教了一辈子体育。退休之前,他是我们当地体校的教练,执教一项小众球类项目,属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一部分。他的女子球队曾经拿过全国冠军。那时我还小,记忆零星,只听他提起过一两次。等我再大一点,想起来了,追问他,他先是愉快且不失骄傲地讲述一番,很快情绪又下去了,偏过头,摆摆手,莫提当年勇。
老爸自己不是学体育的,大学修的地理专业,毕业后回到老家镇上当老师,遇见了我妈,于是有了我。也许是篮球打得好,会写文章,还习得一手好字,总之,他被调到了体育局。
老爸教了一辈子的那个球类项目,他自己没打过,更没上过场。我甚至怀疑,在上岗之前,他可能都没听说过有这种球。长大以后,我问他是怎么教学生的。他说,看书,看教学光碟,然后就可以“纸上谈兵”了。
如今他退休了,是和老妈差不多同时候退的。老妈有时会出去旅行,他不去,在家泡茶、搞卫生,下楼散步,说自己还有很多心事,都办妥了才有心思去玩。年轻时的光彩早就淡淡散去了,时光让他变回了一个平凡的中年人,现在是老头儿。我们已经很久没就体育运动聊起来了,不过昨天打视频电话时,他还给我们“晒”他的新运动T恤,后背印着“CHINA”一词。
在我成年之前,我们一家四口,包括年迈的奶奶,住在体育场的单位宿舍里。这是八九十年代典型的单位职工宿舍楼,楼道里黑洞洞的,各户阳台上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鞋袜,种着广府地区随处可见的杜鹃花和仙人掌。站在我家阳台上,可以毫无遮挡地眺望整个运动场。起大风的时候,大门会被吹得砰砰作响。
运动场的另一端,是老爸球队的露天训练场。记忆中是用黄土填平的泥地,一到下雨天,泥土被水浸湿,变软了,一脚下去就是泥泞。球场边上是一片野草疯长的荒地,长着茫茫一片数不清的含羞草。轻轻一碰,它的叶子就会卷曲合上。天气好的时候,我放了学就会去找老爸,把书包往石凳子上一扔,随手捡一根光秃秃的枯枝,打含羞草去。
有时我会跟着老爸去巡查宿舍。女生宿舍一进去,就是一个大观园。在训练场上,老爸凶得很,学生们都怕他。离开了训练的场所,她们又都围着他。她们大多活泼开朗,哈哈大笑,有着普通女生不常见的健美和帅气,真好看啊。她们伸出指头挑我的小脸,递零食给我,我害羞,躲在老爸的身后紧紧抠住他的衣角,探出一双眼睛好奇地观察她们。
读四五年级时,我遇到老爸来班上选苗。五六十个孩子齐刷刷地起立,老爸穿梭于其中,神情严肃,假装没有看见我。据说全红婵是在课间跳格子时,因惊人的弹跳力被选中的。老爸挑选苗子,也有他的法子,其中一项就是看小腿肌群。小腿上的那一小坨肉,如果位置靠上,又结实紧致,就说明能长高,弹跳好。不然就是“大软脚”,长不高的。而我就是一个“大软脚”。
这不妨碍我跟随老爸参加训练。老爸的球队兼打篮球,偶尔充当篮球队上场比赛。我练的就是篮球。老爸给我们示范了一遍三步上篮,我接到球,向前迈出两步,起跳,上篮,学会了。我可能是他学动作最快的学生之一。
但我跑动不行,老爸常说我的腿绷得太紧了,得放松一点,可我一直没搞懂怎么样才算是放松。我是个总放松不下来的人。最终我也只会三步上篮和一点笨拙的过人技巧,要升六年级了,老爸说学业为重,终止了我的训练。
我跟老爸开玩笑说,要是学习不好,我就打篮球去了。老爸不以为然,说“大软脚”是没用的。是的,我果然没长高,并且骨架小,天生脆皮,风一吹就倒。你如果在现实中认识我,不会觉得我跟体育运动有什么关系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,我是个病猫。
我没记错的话,那是一个穿短衫短裤的夏天。体检医生往边上的空地一指:你去那做十个深蹲。我不知道深蹲该怎么做,大概就是蹲下起来再蹲下起来吧。于是我乖乖走过去,在同学们咯咯咯的笑声中做了十个并不标准的动作。随后医生又给我作了检查,对我妈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。直觉告诉我,我又摊上事儿了。
那年我十岁,四年级,在我妈的班上。我已经很会生病了,还有冷不丁的闯祸。前一年,我接住从蚊帐顶跌落的猫咪,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痕,当即见了血,打了当时被称作“狗针”的狂犬疫苗。那时大家都说,打“狗针”会变笨的,为此我吃了不少天麻炖猪脑。为什么大人们会觉得吃猪脑能变聪明?我也不清楚,但天麻炖猪脑确实好吃。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我害怕这个充满病毒、细菌和冷空气的世界。
到了冬天最冷的日子,老妈会给我穿上一件打底衫,套上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褂,最外层是一件羽绒服。直到裹成一只粽子,我才能去上学。我偷偷观察过身边的同学,他们一般只穿一件毛衣,顶多两件。只有我,三件。对一个要强的小孩来说,这跟丑陋的疤痕一样让人不安。
南方湿冷的空气,既不似陨石的撞击,也不是如箭般直穿过脏腑,而是像毒液一样缓缓渗透,漫过层层的衣袖,浸没皮肤,漏进骨髓里,冷到深处就变成了细微而连绵的疼痛。我动了动喉咙,干干的,它可能又要红肿发炎了。
我熟悉每一家医院和门诊部。我看过许多医生,有人民医院的专家医师、门诊部的普通医生、退休返聘的名医、药店里的驻场郎中,乃至隐居于某个宅邸深处的神秘中医。我吃过同样来路不明的民间偏方,是一种据说治疗痛经的药粉,灰褐色的外表,在药包里堆成一座好看的休眠火山。家里有个爱生病的孩子是这样的,爸妈开着摩托车载着我,踏遍这座小城的东西南北。
那天体检过后,我妈把我载回家,一家三口开了个短平快的家庭会议。我只记住了一个词,心律不齐。也就是说,我的心脏有时会停拍。对于这种似病非病的存在,我们缺乏认知。这是什么意思?我还能打球吗?还能玩捉人游戏吗?这些问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,我把它们都咽到肚子里去了。
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侧卧着,听到心脏如鼓点般咚咚咚地跳动着。我以前也经常侧着睡,怎么就没发现这声响是如此的清晰呢。它不停地从内部撞击我的身体,像是我把它关在里面似的,暴戾地呐喊着。偶尔的停拍,像一段漫长的真空,把我吸进黑洞。它忘却了本该熟稔的旋律。
我翻了个身,那搏动的声响依然没有消失。我猜它是故意的。我一骨碌从黑暗中下床来,跑到爸妈的房前敲门。老妈在里面问我怎么啦。话涌到嘴边又蒸发了,我说,我怕鬼。
后来的那段日子,老妈经常载着我去人民医院看医生,检查,复诊,吃药。再后来就不去了。我不知是我病好了,还是没得治,还是那医生不靠谱。没有人明确告诉我答案,我也没有去问。它似乎凭空消失了。
老爸还是带我打篮球,也许他们相信,运动能让我的身体素质好起来。上初中了,我的体育成绩没有很好,篮球赛才是我的主阵地。老妈嘱咐我,你心律不齐,不能过分剧烈运动,累了记得换人。我点点头,答应了。但上了场后,我就彻底忘掉了这件事,只想上篮,进球得分。隔壁班的同学说我打球特别“狼”,“狼”就是凶狠的意思。
篮球赛过后,我十四岁了,进入青春期,突然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这个人长着海草般的披肩长发,沉默地穿过阳光直刺、风声呼呼的长廊,逃到文学的世界中去,探问自己到底是谁,内心在噼里啪啦地发育,身高却几乎没再长过一寸。
篮球开始在我眼中失去魅力。我也不再相信,运动可以让我的体质好起来。咽喉炎和肠胃炎轮番统治我的身体,一到医院就是挂水。护士说,你的手腕好细呀。又说,血管怎么这么细,我都怕针头扎不进去,你把拳头再捏紧点。我不断从他人口中确认自己“娇小纤弱”的特质。
对于发生在我内心细微而根本的变化,爸妈表现出了中国父母常见的困惑与迟钝。他们突然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语言与我交流,话语变得笨拙。而我也是如此。我们仿佛丢失了十几年来形成的共同的语法。我投身于名为成长的海洋,独自一人。
体育场,我物理意义上的家,为我的青春期提供了唯一的庇护所。晚饭后,夜幕降临,运动场上亮灯了,民众如鱼群般涌入。体育场大门外停满了摩托车和小轿车,夹杂其中的是各式摊贩。我经常下楼散步,从体育场晃荡到马路对面的体育馆,到处都是喧嚣的人群。烧烤摊上仙气腾腾,肉串被烤得滋滋作响,混在油烟里冲鼻的香气萦绕不散。我也是人海中普通而踏实的一员,这让我感到安心。
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,每到学业繁忙或压力增大时,我比平时更容易生病。可我对此束手无策。这次是到了备战中考体育加试的时候,我开始频发神经痛。激烈的跑步或跳绳之后,心脏周边如蜘蛛网百转千回地纠葛在一起的神经,就会“搭错线”,伴随着心跳的节奏,突突地痛起来。我只有蹲下,含胸,把头埋起来像个鸵鸟,才能好受一点。
老爸联系到心脏科医生,给我约了一个24小时心电图检查。这是一个轻巧的装置,往身上涂一层凉丝丝的凝胶,吸附其上,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检查结果可以说很好:窦性心律不齐,良性。我的心脏有瑕疵,这辈子是当不成飞行员了,但正常生活没问题。
我很难描述此刻的感觉。老爸以他一贯的云淡风轻对我说,囡,不用担心,你没事的。我心里知道,压在我们家心上整整五年的那块沉甸甸的石头,被轻轻地拨走了。我本来视我的心脏为对手,一直等待它哪天终于爆发,我们面对面地来一场决战。如今它如婴儿般乖巧地躺在我的身体里,甜美而天真。
我的体育加试成绩接近满分。这一年是2008年,中考结束,北京奥运会就来了。
我最喜欢的其实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。相比于北京奥运的盛大、浩荡、浓墨重彩,雅典奥运更像一个轻盈曼妙的序曲。
比如某天,老爸打开了110米栏决赛的电视直播。田径比赛,不就是一群人在那比谁跑得快吗?太枯燥了,我皱了皱眉。鸣枪。起跑了!老爸从厨房里冲出来。刘翔!解说员声嘶力竭地喊。刘翔!老爸也跟着喊。大家都疯了。21岁的刘翔仰着头披上五星红旗,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太阳神。
故事有一个古希腊悲剧式的结尾。四年后,刘翔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,一瘸一拐地蹦到终点,俯身亲吻了最后一道栏,结束了一位卫冕冠军的奥运会之旅。
这一年,中国夺得金牌榜第一,“综合国力”成了一个热门词汇。我的体质并没有因为升上高中而好起来。我已经彻底忘了,自己曾是一个生猛的体育少女,只有倔强的脾气与日俱增,与我孱弱的体质形成明晃晃的对比。
我一度喜欢上了羽毛球。刚好有位省队退役的羽毛球教练,在体育场的球馆里开班授课。老爸给我办了一张卡,买了个好球拍,每个周末提着泡好的茶水陪我去训练。
我再次展露出了体育运动的天赋,又或者,我只是学东西比较快而已。本来占据一上午课时的开球,我学两轮就学会了,能发出不错的球。老爸很高兴。我很快又学会了接发球和正手击球。
但学球的周期太长了。每周一节课,中间遇上我生病,又得停一周。半个月后,我再次回到球场上,发现自己已经没手感了,打得一团糟。
老爸是个急躁性子,中途休息时,一直站在我的身后骂我不好好打。我低头拧着水杯盖子,面对着墙壁,不用回头,就能感知到全场的眼睛都盯在我的后背上。好好好,我也知道自己差劲呀。我的倔脾气也上来了,心一横,把球拍装回到球袋里,斜挎上就往外走。
我快步穿过夜间的运动场,散步和嬉耍的人群如暗云从我身旁飘过,隐隐约约听见老爸跟在身后,用高亢的嗓音继续批评我。羽毛球教练跟上来打圆场,劝导他不要着急。他平时就是用这种不讲道理的铁腕方式教育学生的吗?他不知道我太久没练了一点状态都没有吗?他不知道最失望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?我气愤得忘记了哭泣,只是闷头疾走。
那次以后,我俩心照不宣地没有再提学羽毛球的事,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那张学习卡我没有丢弃,上面来不及打勾的格子,空荡荡的,像个不语的审讯室,折磨了我很久。再后来它也不见了。
事后回想,这场争执毫无必要。但凡我忍一口气,或事后跟老爸说我还想学,他还是会高高兴兴地给我泡好茶水,陪我练下去。又或者老爸来问我还想不想练,我肯定马上说我想。都不要紧的。可我和老爸就是这样的性格,谁也不肯给谁一个台阶下,两块坚硬且棱角分明的石英岩。我不愿意承认,但我确实像我的父亲。
在成长的过程中,无疾而终的事情太多了。成长充满了遗憾,也许这才是成长的真相。我并不是想说一些励志的话。我想说的反而是,有些东西太难、太难去改变了。它就在那里,瘆得慌,可你就是除不掉它。我和老爸之间,始终延续着类似的处理冲突的方式,能说硬话就不说软话,粗暴、伤人且无济于事。
如果说我从这件事中还发现了什么的话,那就是,我窥见了一个近乎赤裸的自己。这是一个常年在多病的躯壳里封锁着自己的孩子,她自信、骄傲、倔强,同时也胆怯、柔弱、悲伤,这种分裂让她迷茫。她心中有一匹难驯的野马和一只瘦小的羔羊,无法把相反的特质糅合成更加强大的自己。这可能会成为她一生的功课。
“我最后问你一次,真的不考公务员或教师编了吗?我想再听一次你的回答,以后我们再也不问了。”老妈发来问候。这个时候,我27岁,辞掉国企的工作,来到深圳待业。
“不打算考了。”我对她作了最后一次认真的解释。体制内的工作,我确实是不考虑且无向往的。老妈有时会说起,谁家的女儿考公上岸了,就在隔壁的市里上班,周末一家人开车出去自驾游。我告诉她,你的女儿不是这样的。
在择业的事情上,我始终对父母有着一份暗暗的愧疚,我总是让他们忧心忡忡。这份愧疚的心态,我一直“隐瞒”着自己,只在潜意识里运行。而在自我意识当中,我清楚地知道,应该由我来决定自己的人生,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。我不必因此对任何人说抱歉。
可我有时也会闪过一丝心慌。要是回老家或在省内某个地级市,考一次不成就再考第二次,总能上岸的。这样我就能拥有一个相当稳固的饭碗,过上稳妥而体面的生活。我不可能这么做,而这正好暴露了一个我更不愿意看到的阴影面:
作为一个体制内家庭出身的孩子,我对稳定和安全有着本能的依恋,我害怕不确定性,我害怕努力了却失败,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冒险者。这一点,像无形的家庭资产一样,从爸妈的手上传承给了我。
人生继续向前。我转过行,也结了婚,养了一只可爱的猫咪。生活变好的证据还在于,爸妈的工资也迎来了翻番,住进了四室一厅的小区房。我们终于不再为钱所困了。我爸渐渐老了,早就不带球队了,退居二线,过起喝茶看报纸的办公室生活,直至退休,脾气变好了,家务也做得勤了。
不过有些时候,他们似乎还停留在零几年呢。比如我和我先生出去吃东西,拍照给他们看。看到冰淇淋,他们说,这么冰,肠胃受得了吗?看到涂着厚厚的辣椒酱汁的路边摊烤串,他们说,卫生不,不会肚子疼吧?他们忘了我已经不是病猫了。
记得大二有一段时间,我对自己的体质有种近乎魔怔的忧虑,包包里常备肠胃药,发现不好的苗头就迅速掐灭。有次在小姨家,准备出门探望我不常见的亲戚们,我先吃了一粒整肠丸,镇场。小姨笑我,有没有可能你不吃没事,吃完反而肚子疼?
我不知道,我不敢试。我有时会毫无征兆地突发肚子痛,不是锥子钻或刀绞的痛,而是从肚子深处渗出的钝痛,抽走了我的体力,然后是视力。眼前逐渐模糊,意识在流失,我扒出药瓶子胡乱吃了两粒,静待潮水退去,没有别的办法。身边没有人会像我这样。我恨我的躯体。我恨我日渐萎缩的怯弱的灵魂。
后来我还开始严重失眠。说来好笑,失眠的直接原因,是我想治好自己的入睡困难。我试过无数的方法,数绵羊,深呼吸,听钢琴曲,睡前拉伸运动,都没有用。结果越陷越深。后来到了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老师的程度,因为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还无法入睡之后,我的肌肉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。
心理老师是个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姐姐,看着既不热络也不冷漠。我喜欢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。她说的话,和我在心理学书籍上看到的一样。但情绪有了被看见的出口。她说,如果你过分关注身体的某个部分,它会得寸进尺地占据你的注意力。我问她,我经常突发肠胃炎,也是一样的么。她说是的。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,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就等于得到了支援。
那天晚上,我睁眼盯着天花板,什么都不干,什么也没想,直到三个夜猫子室友都已安然入睡,倦意终于席卷了我,把我包裹在寂静的黑夜里。第二天起来,我把肠胃药从包包里取出来,狠狠地压在了箱底。
我尝试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,我已经很久没敢这么吃了,包括在粤语语境里,寒的、热的、湿的,我都去吃。我的肠胃需要这样的锻炼。我还开始增加运动,跟随体育老师早起,到操场上跑圈,跑到几近虚脱,开肩,压腿,在大树底下做瑜伽,冥想,直到太阳醒来。
我开始掌控自己的身体。这种对身体的“胜利”,是我从未有过的,这让我感受到了内心生发的笃定的力量。后来,我把它称为“柔韧性”。
我最喜欢的球队之一,克罗地亚,就有着这种“很弱又很强”的柔韧性。它总是踢平,踢到加时赛,踢到点球大战,却能在最后一刻踢赢。
也许生活就是被打倒,又站起来,如此反复的过程。我可以同时是柔软的羔羊和无畏的野马,前者不会让我羞耻,后者也不会让我狂妄。有什么都放马过来。
我亲爱的老爸早就不打球也不看球了,他最近的爱好是修缮乡下的老屋子,他说老屋翻新好了,他就没心事了,可以戒烟了。我能想象他说完这句话,当即抽出一根烟点上的样子,烟雾从他口中徐徐吐出,他一定又想起了一些往事。
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,老爸得到过更好的发展机会,需要调到外地。后来他说,我那时太小了,他舍不得走,想陪伴我成长。而我记忆中的版本是,在KTV告别会上,老爸和学生们唱了一首又一首歌,最后他和学生们都哭了,我也跟着哭。他最终没有走成,在老家县城当了一辈子教练,一件运动服可以穿二十年。他被留在旧时光里了。
奶奶过世以后,体育场的旧房子,我们就不再住了。房子打折租给了小姑,她陪孙子在城里读小学。我去过几次旧房子,搬走了一些旧物,主要是书、笔记本和老照片。
我翻出了一张五年级时拍的照片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V领黄色外套,短发落在耳后,腋下夹着一只篮球,眼里含笑,神采奕奕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,原来体育撑起了我阳光和坚韧的一面。
我们还把爸妈年轻时的照片都看了一遍。我先生说,爸妈当年的精气神,比我俩都好。那时爸妈还很年轻,那时世上还没有我。
有次我和老妈开车去外婆家,车子驶在高速公路上,坐在副驾驶的老妈突然开口说,“我年轻时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店”。该下高速了,我打开右转向灯,减速驶入匝道。
“哦,是吗?我记得你以前说是想当医生的。”
“那是因为外婆身体不好,我想当医生给她治病吧。”
我想起了一些遥远的不起眼的旧事。老妈说读师范不用交学费,她就去读了,十九岁就出来工作。我喜欢买好看的笔记本,抄写喜欢的诗和句子,老妈说,她以前也好喜欢摘抄。这些都被小时候的我忽略了。那个幼稚的小孩以为,父母从来是父母,孩子一直是孩子。
“哦。”我答道,等待她继续往下说。可是她没再说什么了。
那老爸年轻时的梦想是什么呢?我真不知道。我有时觉得自己无比了解他,有时又发觉对他一无所知。
爸妈的老年生活将怎么过,我的人生又将如何继续,我也不知道。关于未来,我一概不知,除了时常失踪又终能寻回的勇气,除了永不熄灭的期待。
本故事由导师指导完成
9月16号-29号,即将开始
收录16场关于“写作和生活”的真诚对话
三明治首部创作者访谈集
责任编辑:
更多竞猜资讯直播赛事尽在江南体育,江南体育官方网站每日更新2024最新赛事!